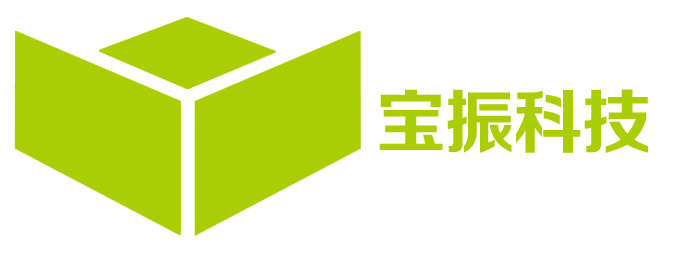- 2023-10-28 垂直绿化植物墙除视觉效果的作用外其他作用
- 2023-10-28 户外垂直绿化墙立体花盆适合种什么植物
- 2023-10-28 道路立体绿化组合花盆在道路绿化中的使用
- 2023-10-27 城市绿化建设走向立体绿化组合花盆空间
- 2023-10-27 办公室打造垂直绿化植物墙可缓解员工压力
大地景观正发生立体绿化花盆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 厦门宝振科技
9月16日,“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进行到午后,一个叫俞孔坚的人的讲演,让困乏的听众为之一振。他使用了大量幻灯片,从航拍照片讲起。
“这是我从100米高空拍下的杭州,毫无规划、杂乱的建筑,水泥丛林,到处都是覆盖物,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还像人间天堂,简直像地狱!”
“这是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城市无节制地快速蔓延,土地上都是建设区,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和让人生畏。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国人的身份和处境。”
“去年,‘神舟’五号上天,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可是,看看这张从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
演讲中,俞孔坚笑容可掬,言辞犀利:
“高速城市化扩张,使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等土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大地景观正发生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我们在任意地虐待、糟蹋着有限的土地。
“土地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死猪肉,一块块切割掉、卖掉,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变得支离破碎,把土地的血脉切断了,破坏了山水的自然格局。古人说了,断山断水,是要断子绝孙的。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我们的城市也将是死的。”
“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年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看看要建的央视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这是在建造一个展示性的传媒帝国的形象。
“当西方人在炸掉他们的人工河渠,埋掉高架桥时,我们却在花大把大把的钱,重复着100年前美国人犯过的错误……”
会后,我追踪采访,一路追到北大他的课堂上。
俞孔坚,41岁,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
“我当时特别着急,着急回国。”俞孔坚是国内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学子,之前他学的是园林专业。1997年,俞孔坚回到了北京。
“回来一看,中关村一带拥挤不堪,路上跑的都是卡车,运砖头、石头,运建材呀,可以说是一种蓬勃的景象。但同时我又看到,行道树正被砍掉,民工们正往河底灌水泥,给河道做护衬……”
俞孔坚说自己当时有一种不安感。“我能看到一个将要发生的前景:一个改造整个国土面貌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但这种改造,又是多么缺乏景观设计的理念。合理地进行土地的设计,正是我所学的专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有过一次很大的环保运动。卡尔森写就了著名的书《寂静的春天》,第二本与之媲美的就是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
“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使我从传统意义上的园林,真正走向了大地景观。麦克哈格说:大地是有内在价值的,土地是有生命的,它是个活的系统。这个活着的系统告诉我们在大地上该干什么,人跟土地的和谐关系是什么样的。思考方法是把仅有的生态学认识,通过叠加的方法,就是千层饼的方法,一层一层叠加,最地下的是地质、地貌、植被、水文,然后动植物的分布,人的活动,一层层叠加,进行土地的适宜性分析,根据这些告诉人们该如何利用土地,该保护什么。”
回国后的几年间,俞孔坚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更让他痛心和焦虑:“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三通一平’掉了;本来非常动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粮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
“广场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着,“中心广场”、“时代广场”、“世纪广场”、“市民广场”,一个比一个气派,一个比一个恢弘。而用俞孔坚的话说:造了一些“没有人性的广场”、“无人的广场”。从7年前回国的第一天起,俞孔坚就对这些城市误区不断地批评。
本来,为市民提供一些活动场所是好事,可是,许多城市广场,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建的。是为了美化城市,是为了展示、纪念或面子,是为了炫耀政绩,而不是为了功用,是为了广场而广场。
“你会突然在郊外稻田里,看见一块花岗石铺地的广场;烈日炎炎下,广场成了可怕的去处———能晒死你!是一块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的热锅。没有树阴供人遮阳,没有座椅供人歇息,铁丝网将人拒草地之外;为了美化广场,不惜巨资,修建大型喷泉、华灯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机关,但又不堪沉重的日常运行费,不得不闲置或偶尔做做展示。将户外广场当成室内厅堂来做,金玉堆砌,以贵为美,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石铺地,整得比抽水马桶还要光滑。好了,下雪了,下雨了,成了溜冰场,老人孩子是决不敢上去的。因为将商业活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排斥在外,夜晚的广场,华灯下也是一片死寂……”
在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广场是一个摆设,市府主楼是最好的观景点。“就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的窗户里看到花园最好的图案一样。”
广场是人与人交流的场所,使用者是普通百姓。“他们可不是坐在市政大厦中俯瞰广场的市长,也不是坐在空调车内绕场一周视察的官员和富豪。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们、女人们、儿童们、老人们,还有残疾人和病人们。广场是为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娱乐设计的,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而那些讲究气派、展示性、纪念性、标志性的形象工程,最后只能成为失去意义的摆设,成为失落的场所。”
在《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俞孔坚和他的伙伴李迪华直言不讳:实际上,是市长们在设计城市,建造什么是领导说了算。在市长们的观念里,仍有封建专制意识在作祟。
长官意志。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听上面的”。惟官是从屋顶种植花箱,官大于法,城市卡盆套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才出现了种种讲究气派、展示和纪念性的城市景观。
草民意识。在封建立体绿化专制社会,君主和官僚治理民众如“放牧牲畜一般”,马克思说过,专治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官僚们的潜意识会经常影响城市建设,使城市景观根本漠视普通居民存在,不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服务。为了获得上级的欢怡、赞赏,可以牺牲万民的利益。
100多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美化运动”。借着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城市形象冲击,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运动”,仅持续了16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经济、美学、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
俞孔坚说:“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
如何帮助市长们避免有害的长官意志,俞孔坚著书“与市长们交流”并为市长们讲课,传播生态与人文理念。因而被挽救的河流、被改建的工程也有不少。在广东的中山、浙江的台州、江苏的宿迁、山东东营……一些绿色项目正造福于民。 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
在北大的课堂上,有人问俞孔坚:为什么说央视新址这样的大楼,在西方,现在是不可能建的?
“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它们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图有其表而已。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样的项目,就是国内的开发商也不会建,它们最终只能让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俞孔坚又解释说,城市只不过是后来植到土地上的,城市发展经历过3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是为神而建的,像中国的天坛、欧洲中世纪的神殿、南美洲的玛亚神庙,等等。那都是神统治人的地方,人没有地位,人是神的奴隶。
第二阶段城市是为君主建的,欧洲文艺复兴后,君主取代了神,城市也不是为普通百姓建的,是为君主、为贵族建的。如巴黎就是为路易十四建的,中国的故宫也不住老百姓。
第三阶段城市是为机器建的。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公路是为了跑汽车,摩天大楼用于商贸,追求高效快速,城市建设是管道型的,像纽约等城市就是这样的。城市不是真正为了人的生活、居住,人没有了步行、休闲的空间,人没有了地位,城市也浪漫不起来。但西方现在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认为是美的东西,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已觉察到不但不美,甚至是有害的。你们能想像出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建工程,是什么吗?”
在美国的波士顿,沿海湾地表上有一条架空的高速干道,这条高速路带来的噪声、污染,对城市影响很大。当地政府一直想通过大开挖,把这条高架路埋到地下去,在原地上建一条绿色廊道,自行车道。讨论了十多年,2003年,这个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市改建工程———波士顿环海高架路大开挖工程动工了。这一挖一埋,要花掉200多亿美元。
“波士顿人花这么大的投资,把高架桥埋到地下去,而我们却还乐此不疲地造高架桥。几十年后,我们会不会也像今天波士顿一样,花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再把桥埋到地下去呢?我们是不是在花钱犯错、犯傻。”
“再说央视大楼,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及现代建筑原理。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建筑。它是展高架桥绿化示性的,它是那些‘帝国’的建筑师们,在现在的中国,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 俞孔坚这样评说他的国际同行:“请你们自重,请不要用你们的汉堡包、麦当劳、热狗、法国油炸食品,来填塞处于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中国的开发商和市长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甄别能力,很容易被张扬的、形式主义的建筑和景观设计所迷惑。国外来的设计师们,要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土地,如同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土地一样;应该把自己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坦白地告诉给中国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们。”
俞孔坚说他与多位市长交流过,感觉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通过城市景观来建立政绩,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是在一种盲目和错误的理念指导下,设计城市、建造城市。在这种情形下,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城市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比如河湖、山林、湿地甚至农田等,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谁也不能动。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的波士顿还是个小镇,城市的决策者们在土地还没大规模开发前,先廉价地购得郊外大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沼泽、荒地、林阴道以及查尔斯河谷,他们立法保护它作为永久的绿地系统。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城市扩大了好几倍,昔日的郊外已变为市中心。现在,这块宝贵的绿地,成为市民身心再生的场所,成为波士顿人最为骄傲的“蓝宝石项链”。
“去年那场并不算大的雪,把北京搞成了什么样子,整个交通瘫痪。我们院里的人晚上5点下班,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假如我们有一条绿色廊道,从北京城这头到另一头,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足够了。”
“在加拿大境内,就有一条畅通的自行车道,从东海岸达西海岸。美国也有一条,从迈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建一条条畅通的绿色廊道,它们必须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来,否则未来的代价太大,更何况石油危机迟早会降临。和平崛起,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不依赖小汽车的低能耗交通模式。全城范围内的绿色自行车道网络不但是健康和生态的规划战略,也是一种国家安全的战略。”
“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关于这一点,许多城市决策者似乎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国家近年来在投资上的推动也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如果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在未来的城市环境建设中必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决策者和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城市也就有了美。一个生态基础好的城市,就像一个人拥有健康的五脏六腑一样;而一座城市的生态基础被破坏了,这个城市也就完了,不可能有生机,更不可能持续发展。”
“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俞孔坚是哈佛回来的,非请他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
俞孔坚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
“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体现在城建上,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贵、奢侈,什么就是好的。除了到处建摩天大厦、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外,还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虽然花了很多钱财,但城市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而是日益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除了以&ldquo花球花盆;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俞孔坚还归结出“帝王意识”、“小农意识”、“庆宴意识”、“领地意识”等。
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最能体现“庆宴意识”。俞孔坚不避讳自己出生在农村,正因为此,他说自己对小农意识有深刻了解。小农经济下的人既贫穷又有穷奢极欲的天性。一年中至少可以有一次尽情消费———过年,就要把平时艰辛节俭而得的积蓄在几天内消费殆尽。其中多带攀比和显摆意思,看谁家宴席最大,礼品最丰。
有报道说今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从1984年开始,花坛摆放最高的一次,“神舟”五号发射架达到了17.4米,成为20年来最高的花坛。广场中心花坛喷泉,直径达72米,中心水池主喷高18米……
“花坛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而且年年翻新。今年是五千盆菊花造就的彩凤,明年是十万株五色草堆成的巨龙。‘大庆’、‘献礼’工程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张扬。可是,几天的节日过罢,花凋草枯,剩下的时间里市民们必须面对着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据可信的估算,用于节日设花坛宴的投入,足能为城市建一个不算小的绿地或公园。”
俞孔坚曾提出保护和建立城市生态基础10大措施,比如:保持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不干断山断水的蠢事,让生命的自然过程通道畅通。城市水系如河、湖,是城市最有灵气和风韵的地方,是最美的部分,要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
“我们祖先讲风水,无非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看看,这还叫河吗?”俞孔坚指着一幅照片说。
河道被做了水泥护衬,筑坝蓄水,河岸做了铺装。水与土地的分离,导致河流失去自净能力,加剧水污染程度。流水变成了死水、臭水。光洁的水泥花岗岩护岸,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际,变得寸草不生。一条自然的河流,是城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现在连老鼠也不光顾。俞孔坚认为在大地景观中,生态健全的水系统构成的绿色通道网络,恰恰最具有蓄洪、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
“那你说说什么叫河?”有人反问他。
俞孔坚一口气地道:“我希望看到清沏的流水,河底长着水草、游着小鱼,而不是水泥,不是光亮的意大利瓷砖,不是整齐的美国草,不是漂亮的荷兰郁金香;相反,我希望看到的是当地的芦苇、茅草、水葱、菖蒲……浅水卵石、野草小溪,人们对河流的需要,并不再乎其水多,而在乎其动人的自然野趣。”
曾经水草丛生、青蛙缠月、鱼翔浅底的自然河流,被穿上水泥盔甲,城市最美丽的元素就这样被糟蹋掉了,将来总有一天,人们要为河流松绑。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把上世纪人工建设的“渠化”河道炸掉、拆掉,重新挖掘以往填埋的水系,恢复河湖的自然形态,再塑城中自然景观的热潮。
“我们的城市建设,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老路?”
“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
俞孔坚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城市景观设计,是广东中山市的岐江公园———一个“杂草丛生”的公园。花几千万元人民币,建这么一个公园,上至市长下到百姓,能接受吗?
“不接受,连专家,也是90%的人反对。”俞孔坚笑着说。
公园建在一座废弃的老船厂——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里,这座船厂曾红火了几十年,当年,中山人以能进这家厂当工人自豪。但上世纪80年代末,船厂开始走下坡路,最后不得不解散。1999年,中山市政府决定在船厂的原址上建一座岐江公园。这个设计,是俞孔坚对国内传统城市景观理念的一次反叛,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造船厂的面积有11公顷,在我们之前,有的设计师想在这里搞房地产开发,有的想把这里搞成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岭南园林。总之是把老船厂清理掉后重建。”
俞孔坚说自己头一次去老船厂时,感受到一股社会主义工业运动的震撼的力量。
“船厂挨着一条河,河边有一个湖,船坞面向湖面。空中,悬挂着各种电线,地上,到处是生锈的破铜烂铁,野草啊,砖头瓦片啊、铁轨啊、灯塔啊、船坞厂房都在,断壁上还能看见‘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但就是没有人。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里面藏着一段记忆。我强烈地感觉是要把这里保留下来,我提出,最好能保留船厂的味道,用现代景观语言改造成公园。”
在论证会上,有90%的专家反对。他们质问俞孔坚:你把原来破烂的、生锈的厂房、船坞、铁轨、机械、齿轮等保留下来,用野草美化环境,这不是胡闹吗?你是不是太超前了,你对中国传统园林态度怀有敌意……
“我用的完全不是传统做法。中国园林强调曲折幽深,我全用直线;中国园林强调亭台楼阁,我用的全是现代工业的建筑。这是一种观念冲突,我相信我的设计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有好处的。为了这个方案,我坚持了整整一年,毫不动摇,说服市长、规划局长,最后他们都支持我,实施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好。”
建成的岐江公园呈现出这样的景观:脏的、乱的、不安全的遗留物被舍弃,当地原有的水系和植被、护岸被保留。堤岸上的水塔,经重新包装,成了照亮过去50年岁月的灯塔;旧铁轨下铺满了洁白的卵石,两侧长着绿草,独具韵味。公园里的喷泉不足一米高,小孩子伸手就能够着水……
回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现在竭力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文运动”。
“现在到处是国外的奇花异草,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认了个巴黎爹、罗马爹、纽约爹,却恰恰忘记了自己是重庆人、武汉人、山东人,最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爹娘。人迷失了,没了根,最后只会感到空虚。”
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白话的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而是科学、民主、平民化的精神。这是一个告别帝王和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抛弃帝国和封建主义的时代。科学和民主,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科的革命,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而我也从当代中央领导人和许多城市的决策者的言行中看到了希望。”俞孔坚说。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要想真正回到“足下文化”,设计师就得“认识人性、阅读大地、体验生活”。
1999年,俞孔坚要在邯郸做一个广场项目。到了邯郸,却找不到感觉,找不到地方特色,找不到设计灵感。他和助手决定晚上到郊外露宿,他们住到一个黄土台地上,周围全是农田、草丘,还有好多坟墓,很冷。他们只带了两床从宾馆抱来的被子,露天睡在赵王台的废墟上。
“夜里起风了,四周的农作物在长,小动物们也都出来了,整个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这一夜我们都感觉到了。”凌晨,天蒙蒙亮,一幅辽阔壮观的画面在眼前展现:黄褐色的土地从脚下延伸而去,一望无际的粟垄伸向天边,这是华北平原特有的种植方式和景观,早起耕作的农民三三两两,拉着驴子,犁地、撒种。
“这时,我的灵感一下出来了,脑海里跳出两句诗:一万年粟垄连天,三千载古道成河。我们的设计就在这两句诗上做文章。为了表现一万年粟垄连天的意境,用了大片的茅草代替人工草坪做广场绿化,中间纵横交错着行人通行的白色石板路,一直延伸到高处的台地上,而台地建筑就是邯郸的会展中心。但很遗憾,这个设计最终没能实现。”
俞孔坚对“野草”情有独钟。他说搞绿化,引进国外的花草,很可能水土不服,需要施肥、精细管理,费用也昂贵。“现在生态环境价值观是‘杂草丛生’,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就是最好的绿化。我说的杂草野树,就是指乡土物种。像北京,就是杨柳、榆、槐、椿呀这些乡土物种。”
在北京,俞孔坚做过一个住宅景观项目,开发商想用几百块钱一棵的银杏树搞绿化。俞孔坚说服他用白杨树,开发商一听用杨树,说:我们这可是高档社区,应该种银杏这种名贵乔木才对呀。“我们坚持用杨树,他同意了。原来银杏500块钱一棵,现在这么粗的杨树,30块一棵。杨树林生长得非常茂盛,走进住宅区感觉很好,透出一股独特的北方气质,既有特色又很朴素。”
在北京,他还做一个体现北方河滩的景观设计,再现了乱石河滩的自然景色:夏天,雨水丰润,有清澈的流水;冬天,河岸上裸露出满谷的卵石,给人留下清泉的想像。
哪些是寻常景观,比如哪些东西代表着乡土的北京?
800多年来,北京一直笼罩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所构成的景观中,对这种不寻常的景观纪念,几乎让人忘了平常、真实的北京———平民的北京。无垠而平坦的华北平原,曾经肆虐的风沙灾害,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勤劳智慧的平民百姓;还有高高的白杨林网,灌渠荷塘,方整的旱地水田,连同四合院、胡同……北京,应该流露出北方的朴实与大气。
在“奥运”森林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设计方案中,俞孔坚他们设计的方案“田”,脱颖而出,位列三甲。
“怎样用最小的投入、最经济的方法来营造奥林匹克这么大的绿地,来营造北京乡土的特色?当时我们想到了这个字‘田’。我们的造价,是其他入选方案的三分之一。好多人也许会怀疑这个‘田’的方案,能不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城市才刚刚摆脱田,怎么又跑到城里种田呢?”
俞孔坚说中国人种了五千年的田,最懂得种田了。用种田的方法,造大规模的绿地最经济,可以解决费用问题、灌溉问题,水的利用问题,湿地的利用问题、管理问题等等,最后,还可以获得丰收啊。
“这个方案最后能不能实现,我现在也不敢说。当然,让大家接受还要一段时间,但我想过了,如果北京接受不了,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定要实现把‘田’种到城市里的梦想。”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们日常的需要。一片林阴、一块绿地、一条河流、一块让人身心再生的场所。那里潜藏着无穷的诗意,它一定会使人重新获得诗意的栖居。”
眼下,身为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的俞孔坚,正和同事们忙着招收景观设计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国家太缺这方面的人才了!”
从2005年起,北大将利用国外师资力量,培养中国的景观设计高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