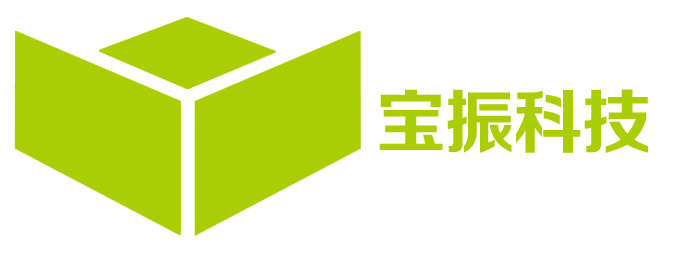- 2023-10-28 垂直绿化植物墙除视觉效果的作用外其他作用
- 2023-10-28 户外垂直绿化墙立体花盆适合种什么植物
- 2023-10-28 道路立体绿化组合花盆在道路绿化中的使用
- 2023-10-27 城市绿化建设走向立体绿化组合花盆空间
- 2023-10-27 办公室打造垂直绿化植物墙可缓解员工压力
城市:生活的艺术与艺术地生活屋顶绿化种植模块 厦门宝振科技
330多年前笠翁李渔完成的《闲情偶记》一书成了畅销书,有精美图文版、还有经典图说版。据说喜欢李渔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抓革命促生产”到“发展是硬道理”,再到今天开始关注生活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进步。
余秋雨先生在《重读李渔丛书》序言中写到:“中华文明在本质上是崇花墙花盆实避虚的,但在它斜屋面绿化花盆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反而产生了一种倒逆性代偿,即不少文人避实崇虚,不愿或不擅对生活实物进行文化关照了”。果真如此的话,如何认识城市、看待城市文化、关心城市生活的问题倒是值得谈一谈了,而将城市作为时空艺术、公共艺术和生活艺术来研究也可成为极有趣的话花柱容器题之一。
一、谁需要“皇帝的新衣”?
我们的城市在丧失特色之后,都想要以建造纪念碑式大建筑的方式,尽快使城市重振雄风、改变面貌。然而城市是一个整体,如果到处都是亮点,也会让人无法忍受,甚至产生厌恶感。
以首都北京为例,保护老北京城的问题争论了50年,至今并未形成共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而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明确制定了“整体保护”的方针后,一个体量惊人的“巨蛋”,作为“国家大剧院”,即将戏剧性地诞生于传统中轴线西侧。这个“巨蛋”的体积庞大、轮廓醒目,与北京的空间尺度、传统肌理、城市形态格格不入。
库哈斯的CCTV大楼方案除了带给人们震撼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在大谈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为了这一视觉上的“震撼”,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将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国家体育场的招标,由两位国际大师——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共同构思的巨大“鸟巢”方案获胜。评委之一库哈斯认为:这一建筑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像的,但确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建造。但是,这个被《南方周末》称为最昂贵的“鸟巢”,在容纳10万人的巨型体育场与温馨的鸟巢之间,极为基本的建筑尺度问题如何能够解决?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认为:短短不足20年尽管房子建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这些未经消化的形式主义舶来品破坏了城市的文脉肌理;为了寻找和塑造特色,决策者不顾一切地推介形象工程,热衷于“有想法”和“不—样”。通过“国际招标”推出的各种千奇百怪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告诉人们,合理的一般都不行,不问功能造价,只要“新奇”就行。
因此,中国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国建筑“大师”标新立异的“试验场”。一个城市没有“大师”作品似乎就是天大的遗憾,评委如果不附和就没有水平。“皇帝的新衣”这个古老童话,成为中国城市的时尚肥皂剧。
二、“建筑面前人人平等”
作家赵鑫珊先生近年来对建筑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献给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新著《建筑面前人人平等》,告诉我们一个极其简单、但是又极为重要的真理:在建筑面前也需要人人平等。上述那些所谓的实验性、先锋派作品,大多是首长工程、形象工程、献礼工程。“公款追星”现象,一些媒体给予曝光和批评,而为官一任,一定要在城市里留下划时代的“纪念碑”,而且还要将自己的审美观甚至嗜好强加于上的行为却极少受到应有的批评。
建筑作为“不可抗拒的艺术”,其投入之巨大、影响之久远,一般人难以想像。有人说: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报了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巴黎罗浮宫金字塔工程所谓的“一箭之仇”,对此评说,本人一直是没法理解的。如果说罗浮宫改建工程是“锦上添花”,“国家大剧院”工程则只能说是“伤口撒盐”,是保罗·安德鲁主张“保护一种文化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险境地”的“无礼取闹”。
事情到此也就罢了,糟糕得是故事还没结束,在各场轰轰烈烈的闹剧热情献演时,建筑大师贝聿铭终于也无法耐住寂寞,85岁高龄重新出山、设计苏州博物馆新址,明知“这块地很重要,特别有挑战性。文化保护区就在里面。拙政园在新馆址的后面,忠王府在它的左面,在这里搞建筑不容易。”还是在故乡的土地上,过了一把瘾。
为建造这一有特殊身份的“中而新、苏而新”的“圣地”建筑,“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历史纪念物,在不平等的状态下遭遇挑战,另外两处保护建筑被迫整体移建,一般民居只能是一拆了之。
即便是建筑大师或老资历的建筑权威,也不应忘记,城市建设规划是建立在那座城市特有的历史条件、时代需求、人文背景等基础之上的,应综合城市独具的市民心理、审美情趣、风俗时尚等诸多要素。
欧美城市对城市景观和历史环境的保护,都是通过严格的城市规划控制来实现的。没有约束,其实是不会有真正的创造的。只有当城市远离了执政者的权力控制,成为非全能之物,并实实在在为市民而建设时,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好的城市设计。
在全球化过程中,地方意识和本土化逐步获得重视,尤其是以唤醒社区公民意识和公众参与为主轴的“社区营造”运动正方兴未艾。城市公共艺术的营造与发展,应以社区参与和公共化精神为出发点。
三、“怀旧热”掩盖下的文化“堕落”
城市作为人与自然共同创造出的作品,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景观。除少数例外,都是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因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城市的各种建筑,不单纯是为某种用途而建造的,它也反映一种艺术美。在整体或局部,呈现出一种文化上的意识。
今天,“城市已不再作为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而是成为一种消费中心;它们也不再作为空间位置和历史事件的网络点,永久地失去了作为流动的公众生活的空间这样一种地位。”
从表面上看,1990年代的社会时尚充满了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变得很怀旧、很有历史沧桑感了,对旧时代之梦幻沉迷不已。老照片、老房子、老电影、老唱片、老漫画……简直到了逢“老”必火的热度。这种怀旧,是因为现实中历史环境、文化遗产消失得太快,人们无能为力只好个人收藏花球容器起“历史”?还是为了将来的升值,把公共的历史文化尽可能地占为己有?没人考证过。只知道,城市中越来越多的“文化老街”——唐宫、宋城或明清街,不过是影视化的建成环境,充满虚伪的氛围和功利的意图。在清宫剧戏说历史的同时,明清街和人造景观也在伪造“历史”和糟蹋文化。
上海“新天地”开发的成功,让城市建设的组织者和房地产投资者都看到了“历史”的经济效益,但是“新天地”更像是欧洲小城里某个温馨的广场,与老石库门其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新天地”不过是由老石库门改造成的供外国人观光和白领阶层休闲的酒吧区。走在其中,我们无法听到历史的呼吸,感受到传统的脉搏。
近年来,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大规模的更新改造,“一个个破落而个性尚存的城市仿佛不约而同地涌进同一家美容院,出来的时候已是清一色的珠光宝气、油头粉面。”普通老百姓感觉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越来越陌生,作为家园的感觉越来越淡薄了。城市正成为人类最大的超级欲望场。
不仅如此,在旧城改造中,经历了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开发,多少历史街区几乎是在转眼之间就在城市中永远消失了,大批大批的老居民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园,带着留恋带着无奈,取而代之的是贵族化空间和镀金的文化。
四、别再把老房子当作“臭袜子”
一个城市没有了人,没有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地域文化或社区文化的存在。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环境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构成了市民生活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是和自然生态一样重要的事物。历史建筑、历史街区是城市设计中的景观资源,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是保持城市特色的物质要素。
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四合院、里弄住宅等普通民居构成历史环境,当作旧城改造的对象,将历史建筑当作危旧房对待。形象地说就是把普通老房子当作了“臭袜子”。
青年作家、批评家余杰在文章中说“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下。其实,袜子有什么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同样地,老房子的破旧不堪,都是人们不当使用、过度使用造成的。
而且,居住拥挤、住房衰败的问题是经年累月形成,要解决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大部分居民属于中、低收入阶层,这种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改善旧城居住环境的最大困难还是经济问题。把一个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的社会工程,当作要在一个短时期实现的建设项目来做,显然是不妥当的。即便是用推土机赶走所有的人,但贫穷依然存在。城市的贫民区也只是转移了,并没能消除。
北京“南池子”工程的本来出发点可能是想进行一种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模式的探讨,在保留历史韵味的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人们感到失望是因为破旧的棚屋消失了,可那些古老的四合院也一起消失了。南池子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它的居住条件比内城其他地区要好得多,人均居住面积近7平方米,几乎是北京内城统计数字的两倍。
如果政府在今后改造旧城区的工作中推广这种自认为不错的“南池子”模式的话,那么,北京就会最终失去它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名城所特有的魅力了。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历史风貌的缺失,城市记忆的不连续,城市文化随老建筑、四合院的消失而流逝。在北京市提出“人文奥运”和“皇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标的今天,南池子改建工程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在旧城更新改造过程中,彻底改变整个旧城破旧的面貌的思想观念,大拆大建、推倒重来的“脱胎换骨”改造方式,正是出现城市特色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将历史环境保护、历史街区整治改善,演变为旧城更新改造,可能会成为在大规模“建设性破坏”之后的、新一轮的“保护性破坏”,对历史街区的打击将是无可挽回的,也是毁灭性的。
五、“深入生活”设计城市
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生活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高质量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城市美最为重要是生活美,现实中的生活是真实的、灵动的。社区中那些细微的事物,街道上所有的一切,生活环境中潜在的东西,它们也许并不亮丽、并不时髦,但却可以推动真正的社区文化的营造。胡兰成在“随笔六则”中谈到:“以前到过的名胜印象都很淡,倒是常走的小街小巷对我有感情。我游过西湖,见过长城,可是动人的只是当时的情景,不是当地的风景。……小时候的为风景所动其实就是努力使自己感动。”只有日常生活,才让人感觉到真实。
美国著名建筑理论家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城市并非树形”。城市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场景、事件和交往组成的网络,一种交换和发展的系统。城市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简单地说,过于规整划一的城市空间,往往缺乏魅力。“凌乱一点才是家”,光彩华丽的往往是“样板房”。
设计必须因地因时因人而异,以一种新方法取代风格的变化。过去,“深入生活”是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今天,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不愿意将自己从事的建筑设计工作称为“做方案”或“画图”,更愿意称之为“建筑创作”,而在所谓建筑创作中卉花盆活动中,最为缺乏得恐怕就是“生活”:对生活的了解、对生活的尊重、对生活的关爱。
正因为如此,Nigel Coates在“街道的形象”一文中提倡:“生活本身是真正的建筑,……让我们运用生活来进行设计吧!”